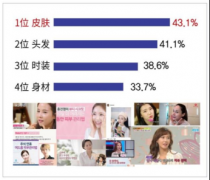从先锋小说的后裔向影视编剧的中生代位移
他依旧是纯文学期刊的常客,但更为人所知的则是《惊蛰》《麻雀》《旗袍》《花红花火》这样的电视剧里的谍战戏、战争戏。远不止是一干知名的演技派戏骨或流量小生从这些剧本中演绎出了若干好角色,关键的是故事本身的逻辑越来越扣人心弦具有了强情节的硬核特征,推着人物于谍海的特殊环境中时刻如刀尖行走或健儿弄潮一般外,也带着包括年轻观众(读者)在内的审美,体验到了国产革命历史题材的类型化叙事的快感,谍战剧情的智力型质地。在我看,这就是故事的技艺,海飞这些年固然谨守着的小说和影视编剧的界限区别,但更多的是共同沉浸到了“故事”的神髓之中。
“讲故事的人”是一个固定概念、一个典故。约翰·伯格、苏珊·桑塔格、纳博科夫都在不同的背景下以此为题、以此为关键词,表达着各自对于“讲故事”的看法。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科夫》中论述了现代社会以来“故事”的状态。他描述的现代,至少包括了印刷术和书籍的普及、新闻报道对于受众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讲故事最要紧的“经验”面临的挑战;“战略经验遇到战术性战争的挑战;经济经验遇到通货膨胀的挑战;道德经验遇到当权者的挑战。幼时乘马拉街车上学的一代人,此时站在乡间辽阔的天空下,除了天空的云,其余一切都不是旧日的模样了。在云的下面,在毁灭性的洪流横冲直撞、毁灭性的爆炸彼伏此起的原野上,是渺小、脆弱的人的身影。”
按本雅明的说法,这些作家个体经历的叙事对于大众是有距离的。故事的地位也在文学的国度里发生着变化,或者说故事的传统是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但有思想的判断是要基于时代社会的总体性变化的,本雅明当年写《讲故事的人》正是基于那个时代节点的媒介、信息和战争,而百来年之后的今天,作用于社会文化的力量元素又有不同,比如影视媒介的资本化兴起,大众文娱对内容产品的刚需,过于专业化的分工对人们知识经验的割裂肢解,竞争性的现代生活亟需故事作为逃避所和补偿器,还有就是国家民族志意义上的“讲好中国故事”等等。这些都在要求故事以新的技术和艺术形式,再次统领公共文化的日常。
海飞恰好在21世纪的开篇从先锋小说的后裔向影视编剧的中生代位移。他的小说即便是与影视同期声的谍战系列,仍然呈现出极简风的峻拔和感受力上的诗意,这是一种现代小说训练有素的教养。具体说,比如其作品中的大热门《惊蛰》等,小说文本终究显得凝练简省,像《麻雀》《惊蛰》《捕风者》《唐山海》《棋手》《醒来》其实都是一个个小长篇、大中篇的量级,其故事、其叙事,内部充盈着文学性:陈夏的眼睛即将复明,“纱布一层一层从陈夏的眼睛上揭开,像揭下她黑暗而绵长的往事”;陈山痛苦地发现妹妹被培养成日本特务的监听员,“他觉得脑门里灌满了蚂蚁,让他的脑袋一阵阵的刺痛”……而他笔下这些谍战小说的英雄们,身处于那样一个动荡年代,大约也总会感到,“这个国家正全身长满了伤口,他就在这样的伤口中进进出出。”
影视的结构要求改造着海飞小说中的情节、细节和人物主次
影视是我们时代的主流叙事形式,尤其是肩负了文化工业和大众市场期待的影视媒介、影视艺术,它对于作家、编剧的考验和改造是巨大的。过去我们习惯从文学、从现代小说的角度否定电视剧尤其是其编剧的文学性,但似乎很少考虑对于讲故事和讲好故事而言,影视的要求才是与远远的故事传统、“讲故事的人”遥相呼应、隔代相亲的,这直接刺激着一套叙事体系和美学特征的创造性生成,改变着之前一个时期作家这个名词的局部定义和工作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