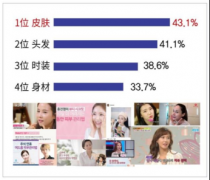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里再唱起《黄河谣》,张佺觉得跟每次演出时候演唱一样,就像是舞台上的仪式,表演前心里总会有期待,精神也要更集中。这首20多年前因为身在杭州思念家乡兰州而写的歌,几乎成为了所有兰州人的公共记忆,也伴随着野孩子这支乐队20多年的更迭,总是携带着很多信息,甚至渐渐与歌曲本身脱离了关系。张佺说希望下次演出的时候,会唱的朋友能一块儿唱,这样这首歌才会更有意义。
这支成立了20多年的乐队有太多的故事,每谈到一个话题,成员都会不自觉地感叹一句“这段很长很复杂啊”。本文根据乐队发展的几个重要地理坐标挖掘故事,关于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事,还在漫长的时间和庞大的音乐世界里等待被一次次倾听和发现。
1 兰州
小城、乐器、注定的相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满20岁的张佺在青海省门源地区做长途公交汽车售票员。难得离开自己的家乡兰州,张佺期盼着车能一直往前开下去不要停下,期盼着去更远更远的地方。但是长途公交汽车的线路只有几条,很快张佺就产生了厌倦,直到认识了几个会弹吉他的朋友。
那个年代吉他正流行,虽然不是人人都会弹,但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几乎家家的墙上都挂着一把吉他。在枯燥的西北生活里,用吉他弹唱一两首歌是最大娱乐,也是骄傲的事情。
门源旁边有一个劳改农场,里面不乏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来的犯人,他们隔着高墙分享流行音乐,还有自己创作的囚歌,也为门源带来了特殊的“都市气息”。张佺最早学吉他,就是跟单位里一个劳改农场释放的人员,对方冲着他的诚意,教了一些基本手法,没想到张佺练得特别认真,经常听着收音机和磁带扒谱子,业余时间全扑在练琴上面。
张佺渐渐厌倦了售票员的生活,1988年,20岁的他辞掉工作回到兰州开始四处寻找在舞厅当伴奏乐手的工作,又阴差阳错地半路改学贝斯,跟着大家一起在舞厅伴奏一些港台流行歌曲。也是在那段时间,张佺认识了曾经野孩子的另一位成员索文俊(小索)。
而与此同时在甘肃小城白银,少年张玮玮的父亲花掉大笔积蓄从广州买了架钢琴给他,把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每天的课余时间都被拿来练琴。小学回家的路上,张玮玮碰到了在街上跟别人打群架、抢了自己零花钱、两家只隔着两排平房的少年郭龙。
2 成都、杭州
漂泊、挣扎、出发的野孩子
当渐渐疲倦了兰州的伴奏生活之后,张佺来到了成都,还结识了野孩子乐队的第一任鼓手周国彬,随后不久小索也追随至成都。
成都那时候物价低、餐饮业发达,张佺觉得每天都有好吃的,收入也不错。那时开始有一些国外的音乐进入,张佺还记得刚去成都的时候朋友给他听了一支叫做Casiopea的日本乐队的歌,“当时被吓坏了。兰州相对封闭,大家都是互相学习和借鉴,并没有更好的渠道去接触音乐。成都的文化更发达,听到的东西更多,所以在成都很有收获,整个过程也特别好。”
从成都开始,张佺和小索开始了乐队的漂泊生活,在每个城市少则停留一两天,多则几个月,似乎跟曾经梦想的生活一步步接近了。随后又辗转到杭州,就这样从1989年到了1995年。那段时间漂泊成为了常态。
在杭州,张佺和小索的收入突然变高,每个月能挣一万多。但是没过几个月大家都厌恶了充斥着醉酒和廉价歌曲的生活,觉得特别不舒服。那时候他们对音乐有了自己的判断,开始觉得生活与内心的审美越来越远。张佺和小索决定离开。在即将离开杭州的那段时间,张佺和小索正式成立了野孩子乐队,并决定去做烙印在他们身上的带有西北民歌风格的新音乐,写了野孩子前期的一些作品。张佺为此写了一首诗《我们走吧,野孩子》,其中写道:“风雪中吹来的孩子,把无羽的翅膀,寄生在文明最糜烂的角落”;“我们走吧,野孩子,就算那条河早已干枯。”
3 北京
沉淀、移居、难忘的河酒吧
回到家乡兰州,张佺和小索用40多天的时间沿着黄河开始徒步采风,收集甘肃和青海本地的民间歌曲元素,也开始正视自己的原创音乐,试着把花儿、信天游、秦腔加入到自己的音乐语言里。在陕北的一个村子里,他们看到有两位老人头戴着毛巾,双手放在膝盖上,一语不发一首接着一首地唱,受到很大的震动,后来在《黄河谣》里,他们也学习了这样的仪式感。这种音乐的形式感动了无数人,也让很多人看到了西北民间歌曲与流行音乐融合的可能性。
兰州的闭塞让他们没有停留太久,野孩子就来到了北京。乐队在旧鼓楼大街附近的地下室住了三年。刚到北京的时候,乐队好几个月都没有演出,加上之前张佺和小索都是在不同的乐队做贝斯手,新组合的乐队需要自己弹吉他,张佺又重新拾起吉他,开始边演出边排练的忙碌生活。2000年左右,李正凯和陈志鹏加入野孩子,也让野孩子的音乐有了更多的突破。后来张玮玮和郭龙也如愿加入了他们仰慕已久的野孩子。
提到在北京的生活,就不得不提到那个被载入民谣史上不可忽略的“河酒吧”。最初只是为了乐队有排练的地方和能有一些收益让乐队在不演出的时候也能维持生活,张佺盘下了位于三里屯南街的这家20平米左右的小酒吧。那段日子,乐队成员们早晨排练、下午休息,傍晚开始营业,直到凌晨三四点,乐队成员们既是表演者,也是服务员。西北人开的店没把赚钱看得特别重,张佺和小索经常会请大家喝酒,每天热热闹闹不知疲倦,苏阳曾经形容说那是“像拉面馆一样的河酒吧”。音乐人们则从天通苑、东北旺各处聚过来,醉了就睡在小索家。彼时还没有民谣这个词,野孩子跟其他乐队一样被统称为地下乐队,在城市最繁华地段,固执地为相同的心灵歌唱。
再回顾河酒吧,张佺和郭龙、张玮玮异口同声,觉得那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才诞生的,以后不会再有了。“但中国这么多城市,这样的酒吧有很多,只不过没人知道而已。是因为这拨人一直说说说,也有人去写,被加工美化成了那个样子。它很好,但并不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与其眷恋河酒吧,不如走到一条江边。”张玮玮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