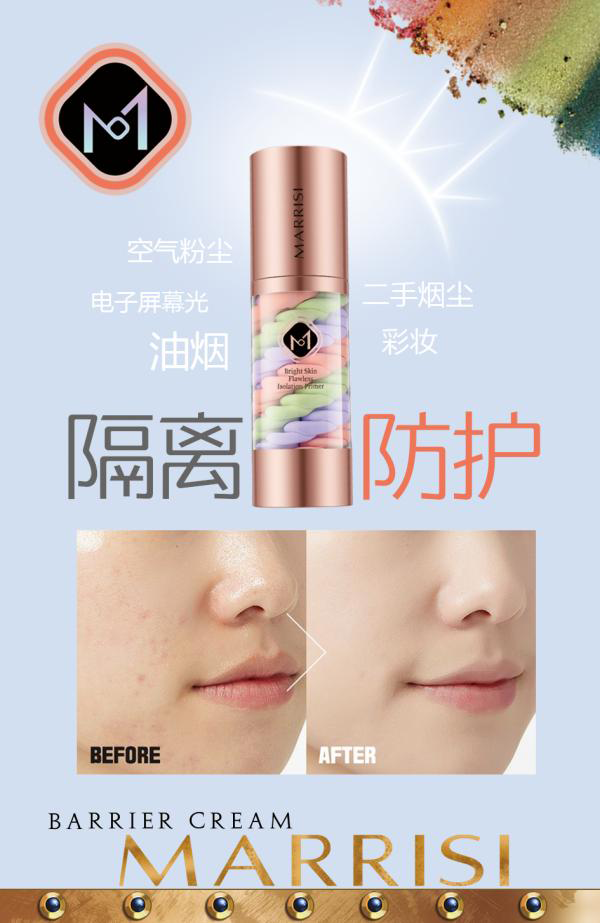喜剧同样苛求一剧之本,创作者需时刻携带一颗细小敏感的心
1993年,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播出,新颖的表达方式和独特的风格令这部长达120集的电视剧迅速风靡全国。自首播已过去了27年,但它不仅是80后、90后的少时记忆,也成为今天00后的快乐源泉。
平凡的老贾家凭何成为这么多人共同的回忆?杨立新很笃定:“喜剧首先是写出来的。”那会儿,英达揣着剧本找到他,“先看看,觉得好看咱就一起弄”。当晚,演员躺在床上读剧本,没看几页就乐不可支,一旁妻子推推他,“明天还上班”。不得已,他憋着笑,抖个不停;再不济,躲进厕所看完了全剧本。“文字都如此鲜活生动,演起来能不好看吗?”
《我爱我家》大获成功后,情景喜剧一度成了创作的显流,可杨立新发现,一些剧本“跑偏”了,人物无特殊性格,戏剧无冲突结构,大段的笑料都“押”在让演员出门就摔跟头之类简单嬉闹的场景里。他推辞了这些剧本,“让喜剧创作更蓬勃,首先需要文学界、作家们多多在生活中发现喜剧。”
演员的话还有另一半,“喜剧也是演出来的”。它并不完全与搞笑画等号,写时需要智慧,演来同样要保持理性。喻恩泰抱持相似观点,《武林外传》里的秀才一角儿让他被大江南北的观众熟知,但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以前一直把演员分为喜剧或正剧演员,后来发现,演员就是演员。”无论喜剧或悲剧,都是在讲述一件事;而演员,无关标签,也都是在表演中体察人的情感、呈现人性本质。喻恩泰拿做菜打比方,“酸甜苦辣咸,有人加香,现在还讲究复合味。我们做戏也如此,有很多复杂的情感,台词之后还有潜台词,喜剧之中看得到悲剧的意味。”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拥有一颗足够细小、敏感的心,能捕捉生活中一闪而逝的明媚因子。
方言仍是塑造喜剧的有效手段,“笑的经典”代表一种生活的真实
王汝刚、张建亚、赵屹鸥、曹可凡……沙龙上,几位上海的创作者不约而同提到了海派喜剧的过去与现在。
王汝刚的印象里,《七十二家房客》是滑稽界老前辈们集体“聊”出来的作品,首演时没有剧本。但这样的模式,到这代人行不通了。张建亚的电影《三毛从军记》是上海电影喜剧一脉的代表作品之一。28年前创作时,正赶上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热播,剧中语言之精巧一时风头无两。张建亚决定另辟蹊径,把默片时代卓别林的感觉融入三毛的故事。“但现在,如果仅仅动用手段已经不行了,我们面对的观众见多识广。”演过话剧、配过音、当过主持人的赵屹鸥坦言,相比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方言,包括沪语在内的吴语方言在喜剧的疆域有些式微了。
如果说喜剧创作的难度是1.0,那么带着浓烈地域色彩的海派喜剧创作难度更上层楼。有没有破解之道?与会者从海派经典里求索答案。
曹可凡提到了桑弧。他执导的《太太万岁》没有一流演员坐镇,但剧本极为精巧,讲女性虚荣,讲社会的欺骗,所有的喜剧结构层层嵌套,作品名动一时。它与《假凤虚凰》以及稍后的《哀乐中年》一样,都是海派喜剧扎根于市井生活、展开市民喜怒哀乐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