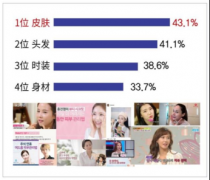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欲望和奋斗都是坦然的
1984年,金宇澄结婚,设宴上海文史馆食堂,新娘子的喜服是亲戚从国外带回的红色开襟连衣裙,款式简洁,剪裁线条大气,温暖明亮的朱红色,喜气也洋气。28年后,昔日文艺青年金先生成了年轻作家们尊敬的“老金”,写成《繁花》。又过8年,为了同名电视剧拍摄,他拿出压箱底的结婚礼服。
时光倒流三十年,上海的凡夫俗子们个个撸着袖子加油干,相信“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梦想,那时的底色,真是一片热情高涨的红色。
1985年,靳羽西为了拍摄《改变中的中国》这档节目,第一次来到上海,当时她的身份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之后,上海举办首届国际电视节,“邀请几十个国家的电视人到这里,电视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上海这座城市敢想敢闯的精气神就此给她留下深刻印象。1993年,她在友人的鼓动下决定“去上海做生意”,丈夫听说她要做化妆品时,惊呆了:“那里没人用化妆品,你卖给谁啊!”而靳羽西气定神闲:“他们现在不用,不等于以后不用。”如她所预料的,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开放之路,总是越走越宽,经济腾飞带动了审美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在南昌路长大的麦女士看着东方明珠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地造起,她在老卢湾的黄金地段开起饭店。她像《繁花》里的李李,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有几个类似“宝总”的能照顾她生意的蓝颜,也能顶着烫了一半的头发到店里应付砸场混混。比起李李心底凄厉黑暗的秘密,现实中的麦女士活出烈火烹油的闹猛生气,拿得起放得下,在店里能紧盯油腻的后厨,卸掉老板娘的工作就出入锦江饭店买最华丽的衫,当年的“九江路精品一条街”落她眼里是“南方一麻袋一麻袋来的货色”,“顶多去复兴路菜场穿穿”。陈先生记得1980年代谈恋爱那会儿,因为烫卷毛、穿太子裤,他被调侃是“时髦小香港”。他的阿姨给他带回的名牌真丝领带,一根领带的价格抵一件皮夹克,他戴着大面积艳色的领带去希尔顿酒店喝咖啡,一杯咖啡要价50外汇券。如今他老了,翻出旧领带与儿子说风流往事,儿子却嘀咕:“太妖了。”
在那个物质和欲望的闸门乍开的年代,闹哄哄的一团,缤纷杂乱的色彩因为热腾腾的生活温度而不显俗气,“奋斗和放纵都是理直气壮的”。金宇澄把这些纷纷乱乱写进《繁花》,有阿宝与李李心意相通的一点温存,也有汪小姐和徐总在酒局中的油腻荒唐,作家不给出高高在上的价值高下判断或社会批判,他赋予这些断章以诗的意义:“人生是这样乱,这样无序,在城市生活中,在读者经验中,实在太多了,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真情实景,因此无意义就有了意义……”